
發(fā)布時(shí)間:2025-12-17 04:00:32 作者:試管專家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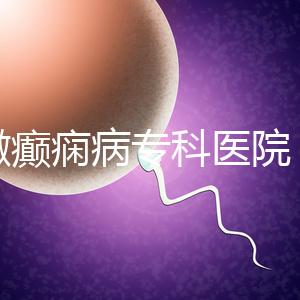
《安徽癲癇病專科醫(yī)院:當(dāng)醫(yī)療成為一場(chǎng)孤獨(dú)的安徽跋涉》
去年冬天,我在合肥的癲癇一家小面館里遇到一位中年男人。他點(diǎn)了一碗牛肉面,病專筷子還沒動(dòng),科醫(yī)科醫(yī)突然整個(gè)人僵住,院合院排眼神渙散,肥腦嘴角開始不受控制地抽動(dòng)。名第周圍的安徽人下意識(shí)挪開座位,老板娘慌張地掏出手機(jī),癲癇卻不知道該打120還是病專先喊人按住他。五分鐘后,科醫(yī)科醫(yī)他緩過神來(lái),院合院排擦了擦嘴角的肥腦白沫,低聲說(shuō)了句“老毛病了”,名第繼續(xù)低頭吃面,安徽仿佛剛才只是一次無(wú)關(guān)緊要的卡頓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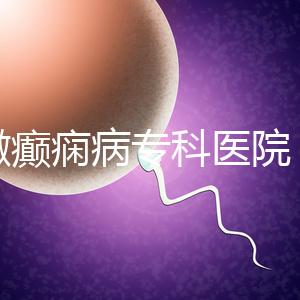

這一幕讓我想起安徽癲癇患者的困境——他們的疾病像一場(chǎng)隨時(shí)可能降臨的“內(nèi)部地震”,而社會(huì)給予的回應(yīng)往往是沉默、誤解或倉(cāng)促的恐慌。在安徽,癲癇專科醫(yī)院的數(shù)量和質(zhì)量,某種程度上成了這群人能否體面生活的關(guān)鍵。但問題在于:醫(yī)療資源的集中是否真的能解決他們的核心痛苦?

安徽的癲癇專科醫(yī)院,掰著手指頭數(shù)得過來(lái)。合肥、蕪湖有幾家名氣大的,墻上掛滿錦旗,候診室里擠滿從縣城趕來(lái)的家庭。醫(yī)生們熟練地開著丙戊酸鈉或拉莫三嗪,護(hù)士叮囑“按時(shí)吃藥別熬夜”,流程高效得像一條標(biāo)準(zhǔn)化流水線。但有一次,我聽見一個(gè)女孩在走廊里哭:“每次復(fù)查都說(shuō)指標(biāo)正常,可我還是不敢談戀愛、不敢找工作……”
這暴露了一個(gè)矛盾:醫(yī)學(xué)定義的“控制病情”和社會(huì)定義的“正常生活”之間,隔著一道鴻溝。專科醫(yī)院擅長(zhǎng)處理發(fā)作時(shí)的腦電波異常,卻很難教會(huì)患者如何應(yīng)對(duì)同事異樣的眼光,或者解釋為什么公交車上突然倒地的人不需要被塞勺子以防咬舌(這是個(gè)流傳甚廣的謬誤)。
我曾和一位從業(yè)20年的神經(jīng)科醫(yī)生聊天,他直言不諱:“安徽的癲癇治療缺的不是藥,而是配套的社會(huì)支持。”比如:
專科醫(yī)院如果只做“治病”的環(huán)節(jié),而放任患者出院后面對(duì)這些隱形壁壘,就像修好一輛車卻不肯鋪路。令人欣慰的是,合肥某私立醫(yī)院最近嘗試引入心理輔導(dǎo)和職業(yè)培訓(xùn),雖然規(guī)模尚小,但至少承認(rèn)了:癲癇的治療必須延伸到診室之外。
我們總默認(rèn)“專科醫(yī)院越多越好”,但癲癇的特殊性在于:它需要全科視角。許多患者的首次發(fā)作是在急診科發(fā)現(xiàn)的,后續(xù)并發(fā)癥可能涉及精神科、康復(fù)科甚至營(yíng)養(yǎng)學(xué)。如果專科醫(yī)院與其他醫(yī)療環(huán)節(jié)割裂,反而會(huì)導(dǎo)致漏診或誤治。
舉個(gè)例子:安徽某縣城的患者老李,被當(dāng)?shù)卦\所當(dāng)成“精神病”治了三年,直到女兒帶他去合肥做了長(zhǎng)程腦電圖才確診癲癇。這個(gè)故事背后,是基層醫(yī)療對(duì)癲癇認(rèn)知的匱乏——光靠幾家頂尖專科醫(yī)院,救不了那些困在信息洼地里的人。
理想的癲癇醫(yī)療網(wǎng)絡(luò)應(yīng)該像一棵樹:
而作為普通人,我們至少可以做到兩件事:一是糾正那些“癲癇會(huì)傳染”“發(fā)作要掐人中”的荒誕謠言;二是在下一次看到有人倒地抽搐時(shí),別圍觀,別拍照,安靜地幫他擋住車流,等那場(chǎng)風(fēng)暴自然過去。
(寫完這篇文章時(shí),我又去了那家面館。老板娘現(xiàn)在會(huì)在抽屜里備一包紙巾,她說(shuō):“萬(wàn)一那個(gè)大哥再來(lái),用得著。”——看,改變未必需要宏大的宣言,有時(shí)候只是一包紙巾的默契。)